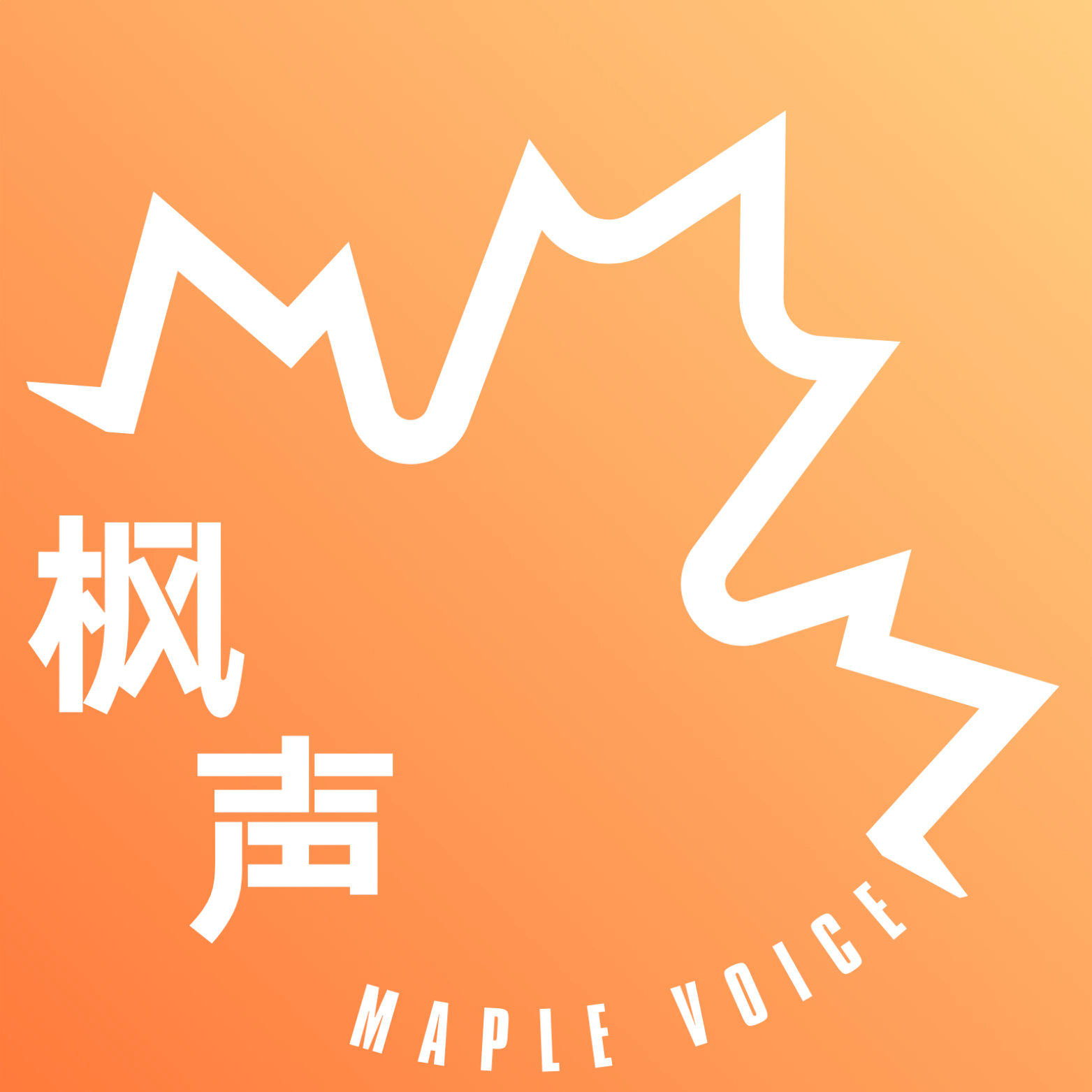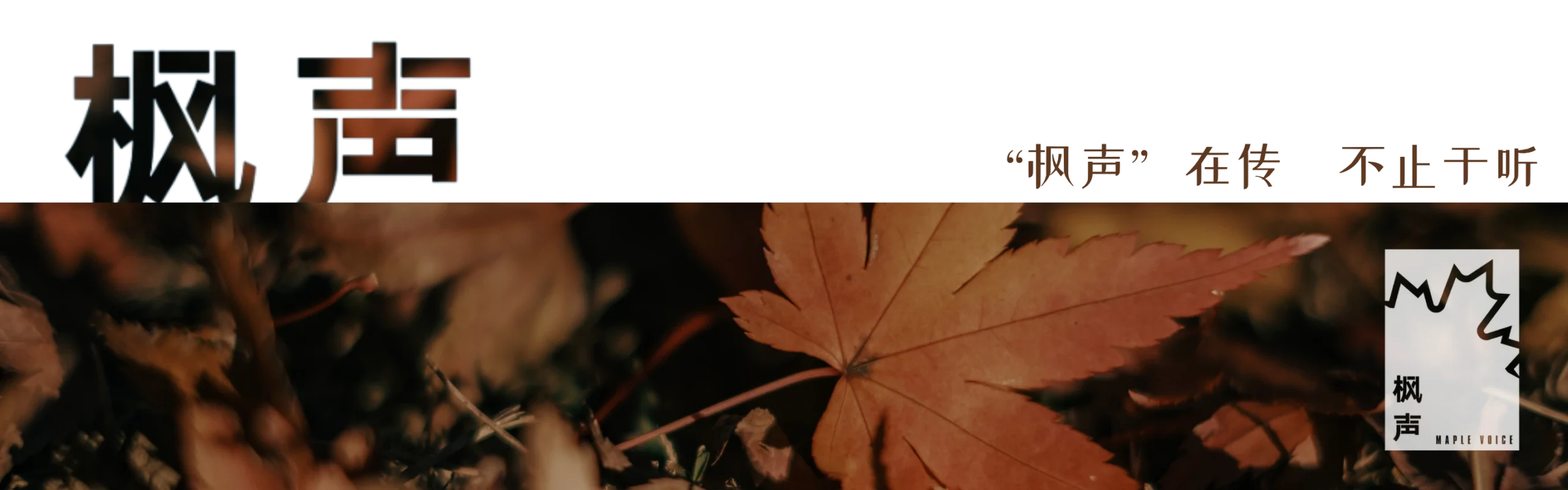一句话概括
过去十五年,中国学生在加拿大的数量经历了一个“先猛涨、后下滑、再小幅回升”的过程。2009年大约只有5万人,2019年冲到14万多的峰值;疫情一来掉到10万左右;2023年还在低位徘徊,但2024年有小幅回升。到了2025年,加拿大收紧学签配额、提高生活费要求,还调整了打工和毕业工签规则,整体氛围是“鼓励高质量,压低低门槛”。
从5万到14万:中国学生在加拿大的黄金十年
2009年前后,中国学生在加拿大只有5万左右。那时,留学加拿大还算“小众选择”,主要是看中学费比美国便宜,签证政策也相对宽松。
到了2010年代,加拿大逐渐成了热门目的地,尤其是和澳洲、英国相比,加拿大的移民通道更友好。于是,到2019年底,中国学生人数涨到14.05万,几乎翻了三倍。当年全体国际学生是63.9万,中国占了22%,是绝对的“大户”。
疫情冲击:人数掉到10万出头
2020—2021年,疫情让航班停摆、签证处理慢,很多学生被迫延迟入学。到2021年底,中国学生人数只有10.53万,比高峰期少了近3.5万。这时候,加拿大整体国际学生规模还在涨,但中国学生的比例明显下降。
2023年:表面没涨,实则很活跃
2023年底,中国学生人数是10.21万,基本没涨。但如果看“全年持有学签的人数”,有13万多。这说明来来回回的人不少,有人毕业离开,也有人新进来。整体看,中国学生群体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,但在流动性上已经开始活跃。
与此同时,印度学生人数飙升到42.5万,牢牢占据第一,中国只能排第二。这背后既有印度申请量庞大,也有加拿大政策对不同生源国的结构性影响。
2024—2025:政策收紧,结构洗牌
从2024年开始,加拿大政府给学签设了全国性配额,目标比2023年减少35%。这意味着,不是想来多少就批多少,得看名额。而且,从2025年起,硕士和博士也纳入配额体系,但专门预留大约12%的名额给研究生。这对中国学生来说,其实是利好,因为中国申请硕博的比例高于很多国家。
另一个变化是资金要求。2025年起,一个单人申请者需要证明有22,895加元的生活费(不含学费),比之前大幅提高。对资金紧张的家庭,这是一个门槛。
打工政策也调整了。疫情期间允许国际学生无限打工,但从2024年底起,学期中最多只能打工24小时/周。换句话说,不能再靠疯狂打工来覆盖生活费。再加上毕业工签(PGWP)收紧,比如公私合营学院的新生拿不到工签、配偶工签也只限于硕博阶段,这些都让“低门槛路径”变得不划算。
为什么人数会这样波动?
如果把这个趋势拆开看,有几个关键因素:
- 政策的方向:加拿大政府想要控制总人数,保证质量,尤其是要缓解住房和医疗压力。
- 经济成本:生活费门槛提高,加上汇率波动,让部分家庭“望而却步”。
- 打工与移民的预期:过去很多人看中加拿大“读书—打工—移民”的连贯路径,但现在中间环节更严格了。
- 国际竞争:英国、澳洲在疫情后抢生源,政策上也有拉力,中国学生的选择更分散。
中国学生的占比:从22%跌到不到10%
数字最直观:2019年,中国学生占所有国际学生的22%;到2023年,这个比例只有9.8%。同样的几年里,印度学生的占比不断上升,几乎占了四成。这意味着,加拿大的国际教育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。
未来会怎样?三种可能场景
到2026年前后,中国学生在加拿大学习人数可能会在8万到11万之间徘徊,具体看政策走向:
- 保守情景:中国份额继续下降到8%,年末人数可能只有8万多。
- 基准情景:份额稳定在9—10%,人数在9—10万之间。
- 乐观情景:研究生名额释放,加上签证效率改善,中国份额回到10%以上,人数可到11万。
换句话说,总体不会回到2019年的14万高峰,但高层次项目的机会依旧稳健。
给家长和学生的几点建议
- 目标明确:如果奔着移民和职业发展,优先考虑硕士/博士或专业学位。
- 预算充分:按生活费2.3万加元+学费来准备,不要寄希望于打工来补差。
- 避开低回报路径:比如公私合营学院,这类项目风险大、回报低。
- 读懂数据:看IRCC数据时要注意“年末在册”和“全年持有人数”的区别,避免误判趋势。
结语
简单说,中国学生在加拿大的数量已经过了“狂飙期”。未来几年,不会再有以前那种暴涨,但高质量、资金充足、目标清晰的学生,依然有稳定的机会。数量上可能比不过印度,但“质量占比”是可以提升的。